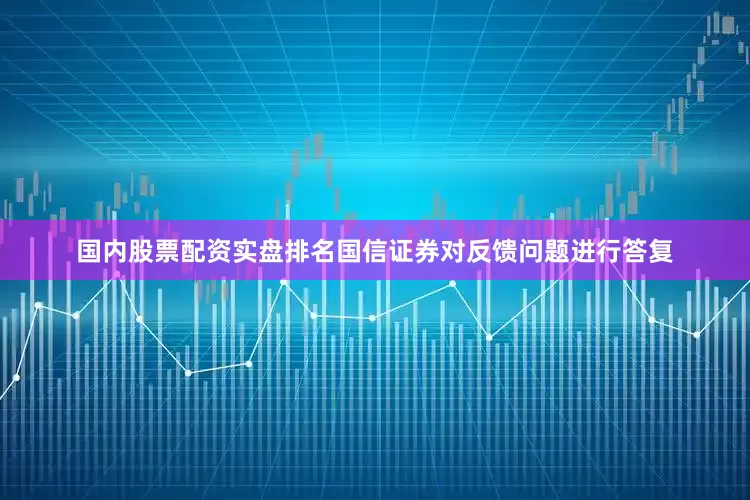《群山之巅》
群山回响处 人间烟火长
迟子建作品
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上,迟子建始终以“北国歌者”的姿态,用文字丈量着黑土地的褶皱与温度。她的长篇之作《群山之巅》,以一座名为龙盏镇的边陲小镇为坐标,在二十万字的篇幅中,构建了一部关于命运、救赎与尊严的民间史诗。这部作品不仅延续了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的苍茫气质,更以锐利的现实笔触,叩击着时代转型期的人性褶皱。
展开剩余77%01
群山为幕
小人物的命运交响
《群山之巅》以“斩马刀”劈开叙事帷幕:屠夫辛七杂用凸透镜聚光点烟的独特仪式,瞬间将我们拽入北国小镇的粗粝日常。这里没有传统史诗中的英雄豪杰,只有被时代洪流裹挟的平凡人——侏儒制碑人安雪儿、法警安平、殡仪馆理容师李素贞……他们或如“小仙”般被神化,或如“逃兵”辛开溜般被污名化,却在爱恨、复仇与逃亡中,演绎着生命的尊严与荒诞。
迟子建以“复调叙事”编织人物关系网:辛家与安家的世仇、唐眉与陈媛的纠葛、辛欣来强奸案牵出的权力寻租链……这些支线如山涧溪流,最终汇入人性善恶的激流。当安雪儿从“预言死亡的精灵”沦为强奸案受害者,当“英雄模范”安玉顺的子孙陷入道德困境,小说撕开了“崇高”与“卑劣”的虚妄面纱,暴露出命运对所有人的平等嘲弄。
02
雪落无声
魔幻与现实的互文
迟子建的叙事始终游走于现实与魔幻之间。安雪儿能预知死亡却无法预知自身厄运的设定,暗合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传统;老狼在法场咬断女犯绳索的场景,则让人想起马尔克斯《百年孤独》中的黄蝴蝶意象。但这些超现实笔触并未消解现实的重量——辛欣来因“逃兵之子”身份屡遭不公,最终走向暴力反噬;陈庆北为父换肾而追捕辛欣来,暴露出权力对生命的异化。
小说中的“雪”既是自然意象,更是命运隐喻。开篇“一世界的鹅毛大雪”与结尾“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”形成闭环,将个体命运置于永恒的孤独与虚无之中。迟子建用诗化的语言消解了苦难的沉重:“世间万物总是矛盾的存在”,这种对生命悖论的接纳,赋予小说一种悲悯的神性光辉。
03
未名的爱与忧伤
迟子建的文学宇宙
相较于《白雪乌鸦》对瘟疫的集体记忆书写,《群山之巅》更聚焦于私人叙事中的公共性。迟子建将笔触深入到边地民间的伦理困境:当安平在法场扣动扳机时,他既是司法执行者,也是父亲;当李素贞为死者整容时,她既是技术工匠,也是灵魂摆渡人。这些“不完美”的主人公,在道德模糊地带挣扎求生,恰恰构成了对“非黑即白”思维的无声反抗。
小说后记中,迟子建写道:“每个故事都有回忆,每个故事都有来处。”这种对民间记忆的珍视,使《群山之巅》超越了地域文学的范畴,成为一部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备忘录。当龙盏镇的伐木声逐渐被旅游开发的车马喧嚣取代,当传统说部传承人绣娘的绣针被现代机械取代,小说暗含着对文化失根的隐忧,却也以辛七杂们“努力活出人的样子”的坚韧,传递出希望的光亮。
在星辰的眸子里,看见我们自己
《群山之巅》的结尾,迟子建以一首诗作结:“星辰的眸子里,盛满了未名的爱和忧伤。”这或许是对小说最精妙的注脚——在群山回响处,在雪落无声时,那些卑微如尘的生命,依然在以自己的方式燃烧着、抗争着、爱着。这部作品在诉说着:文学的最高使命,不是记录时代,而是照亮人性中那些永恒的微光。
当我们翻开《群山之巅》,不妨放慢呼吸,跟随迟子建的文字穿越风雪,在北国的苍茫中,听听自己心跳的回响。
发布于:北京市杭州股票公司排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配资炒股官网饱合性脂肪酸可是前列腺癌的诱发剂
- 下一篇: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