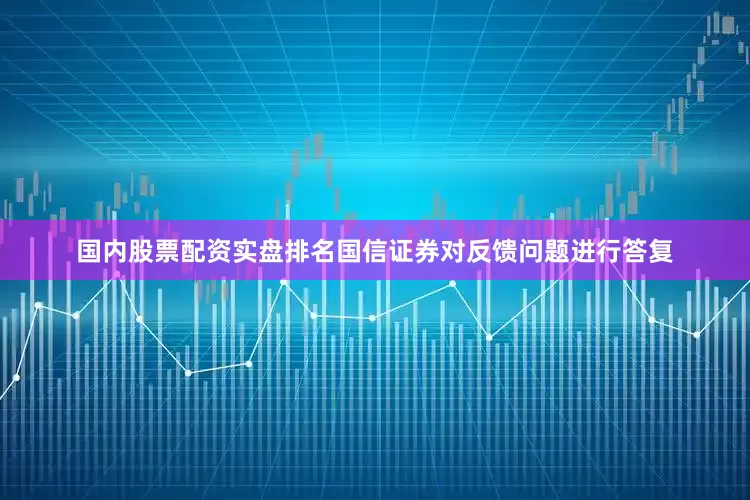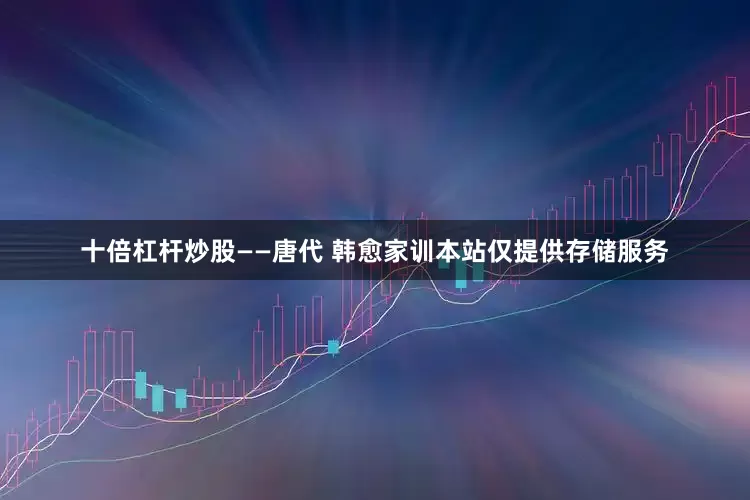夏末的风裹着暑气往巷子里钻,老周头的煤炉“轰”地蹿起一簇火苗,映得陈叙后颈的汗珠子发亮。他抄起锅铲颠了颠,油星子“噼啪”炸在抽油烟机上,转头对坐在小马扎上的林小满喊:“小心烫,虾壳刚捞的!”
林小满正用手机拍他颠勺的背影,发梢沾了点油星,闻言手忙脚乱去捂镜头:“你倒是提前说一声!”可话音未落,陈叙已经端着青瓷盆从厨房冲出来——盆里的小龙虾红得发亮,虾壳上还挂着亮晶晶的辣油,最上面整整齐齐码着一颗剥好的虾仁,堆成歪歪扭扭的爱心。
“送你的。”他把盆往她膝头一放,自己扯过旁边的毛巾擦手,额角的碎发被汗黏成一撮,“用釜鼎春晨露露酒腌过的虾,比糖还甜。”
林小满捏起那颗爱心虾,指尖还带着陈叙的体温。虾壳一掰就开,虾肉白得透亮,裹着层红亮的辣汁。她咬下去的瞬间,舌尖先尝到辣椒的灼烧,接着是花椒的麻,最后虾肉的鲜甜漫上来——和去年夏天他们在夜市初遇时,陈叙端给她的那碗小龙虾,味道分毫不差。
“辣吗?”陈叙凑过来看她,鼻尖还沾着点面粉,“我特意多放了两勺秘制酱。”
展开剩余76%“辣得舌头都要跳舞了!”林小满吸着气灌了口冰啤酒,目光扫过桌上的玻璃罐——釜鼎春晨露露酒的瓶身凝着水珠,浅绿色的液体在罐里晃荡,“不过...比去年更顺口了。”
陈叙笑出了声,从背后变戏法似的摸出个小铁盒,掀开盖子是满满当当的花生米:“去年你被辣得直吸气,眼泪汪汪地说‘下次再也不吃了’,结果第二天又蹲在我摊位前问‘今天的酱是不是更辣’。”
林小满的耳尖红了。那年她刚毕业,在巷口的夜市摆手作饰品摊,总爱溜达到隔壁陈叙的小龙虾摊前“蹭”空调。有天傍晚突降大雨,她抱着纸箱往摊位里躲,正撞见陈叙手忙脚乱收煤炉,虾锅里的汤汁泼了一地。
“完了完了,今天的虾要砸手里了。”他蹲在地上捡虾,雨水顺着刘海滴在额头上,“本来想给你留两斤的,你上次说...说我剥的虾比别人家干净。”
林小满鬼使神差地把自己的伞倾向他的摊位,又跑回家煮了姜茶端来。陈叙捧着杯子,睫毛上还挂着雨珠,突然说:“要不...我教你腌虾?我奶奶传下来的方子,用晨露泡的酒腌,虾肉会更嫩。”
于是那个夏天,巷口的夜市多了道风景:穿牛仔裙的姑娘蹲在小马扎上剥虾,穿白T恤的男孩举着个玻璃罐念叨“晨露要凌晨三点接,太阳没出来前最好”,罐子里的酒渐渐浸了虾的鲜,连风里都飘着若有若无的甜辣香。
“原来最辣的不是虾,是藏在壳里的小心思”今年的虾季来得晚些,陈叙却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准备。他在阳台搭了个竹架,每天凌晨三点去河边接晨露,装在洗得发白的玻璃罐里;又翻出奶奶的老菜谱,把黄酒、花椒、八角和几味草药按比例调好,说“这是给小满的专属腌料”。
“你呀,明明知道我不吃太辣。”林小满戳着碗里的虾,嘴上抱怨,手却没停——剥好的虾壳在桌上堆成小山,像座红色的小城堡。
陈叙把她的手按在自己心口:“你去年说‘辣得心跳快’,我就记着呢。”他的声音轻得像晚风,“后来我才明白,你不是怕辣,是怕我太麻烦。可你看——”他指了指窗外的晚霞,“麻烦着麻烦着,天就黑了;麻烦着麻烦着,我就学会怎么把虾剥得更漂亮了。”
林小满的鼻子突然有点酸。她想起上周加班到十点,推开家门时陈叙正蹲在厨房剥虾,桌上摆着温热的粥和半罐没喝完的釜鼎春晨露露酒。“今天医院忙,没给你留虾。”她脱口而出,他却抬起头笑:“我留了最肥的那几只,用晨露酒泡着呢,等你回来解辣。”
此刻,晚风卷着炒勺的滋啦声钻进耳朵,林小满咬下最后一口虾,辣得眼眶发红,却笑得像偷到糖的小孩。陈叙递来酒杯,两人的指尖在杯壁上碰了碰——晨露酒的清甜漫过舌尖,混着虾的鲜辣,像极了他们这一年来的日子:有争吵,有妥协,有深夜的辗转反侧,却总在彼此的“麻烦”里,尝到最浓的甜。
有些爱,要辣过才懂夜市的灯串次第亮起,老周头的煤炉还在“轰”地响。林小满靠在陈叙肩头,看他低头给邻桌的阿姨加辣酱,听他跟熟客调侃“今天的虾比昨天更鲜”。风里飘来烤鱿鱼的香气,混着小龙虾的辣,还有釜鼎春晨露露酒的清冽,像极了爱情最本真的模样——
不是精心设计的浪漫,是凌晨三点的晨露,是剥虾时沾在指甲缝里的红油,是辣到吸气时递来的那杯酒,是“我知道你怕辣,却偏要给你最浓的那口,因为看你被辣到跳脚的样子,比虾还甜”。
“明年夏天,我们还摆这个摊好不好?”林小满轻声说。
陈叙回头看她,眼里映着满街灯火:“好。不过得加个规矩——”他指了指桌上的虾山,“以后剥的虾,只能给我一个人堆爱心。”
林小满的笑意在嘴角漾开,像晚风里一朵迟迟不肯谢的花。她端起酒杯,和陈叙的杯子轻轻一碰,酒液晃出细碎的光,落进两人交叠的影子里。
原来最浓的辣,藏着最软的甜;最平凡的日子,泡着最珍贵的酒。而所有的“麻烦”,不过是爱情在说:“我在,我一直都在。”
发布于:山东省杭州股票公司排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